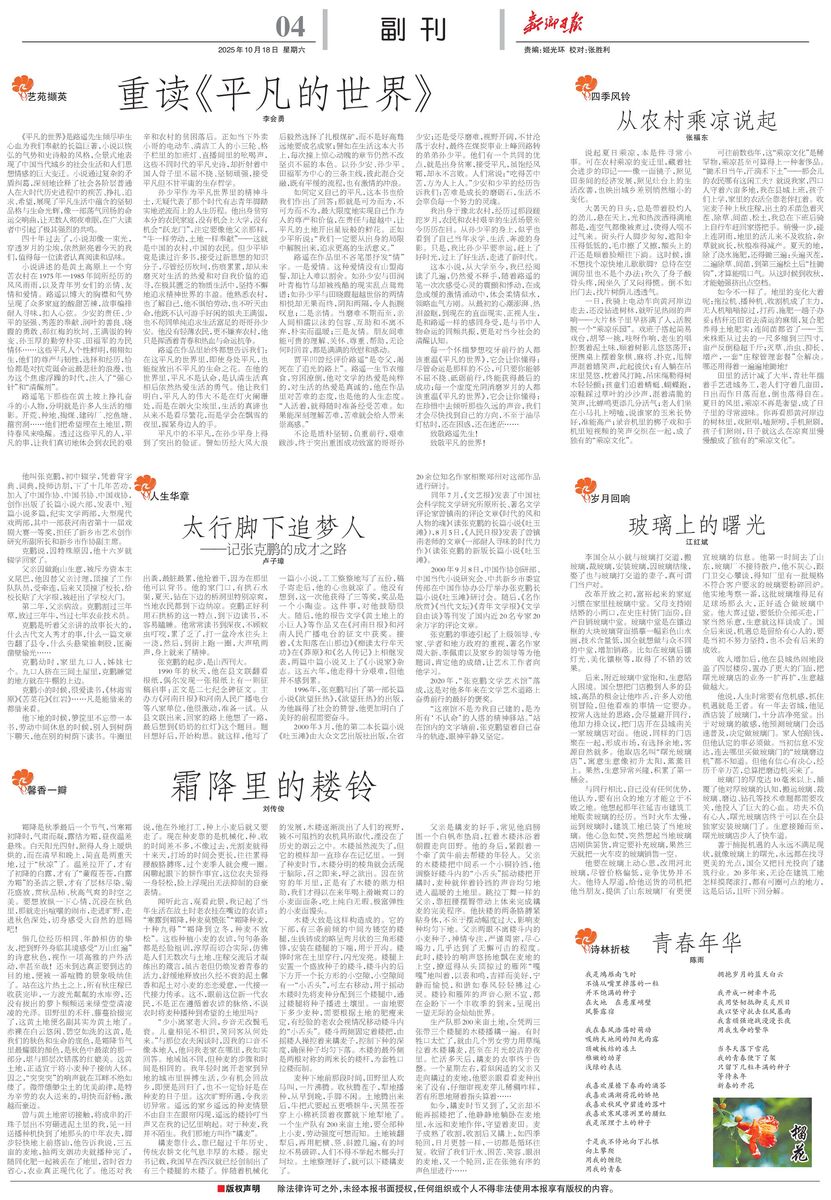从农村乘凉说起
发布时间: 信息来源:
张福东
说起夏日乘凉,本是件寻常小事。可在农村乘凉的变迁里,藏着社会进步的印记——像一面镜子,照见田垄间的经济发展,照见灶台上的生活改善,也映出城乡差别悄然缩小的变化。
大暑天的日头,总是带着股灼人的劲儿,悬在天上,光和热泼洒得满地都是,连空气都像被煮过,烫得人喘不过气来。街头行人脚步匆匆,遮阳伞压得低低的,毛巾擦了又擦,额头上的汗还是顺着脸颊往下淌。这时候,谁不想找个凉快地儿歇歇脚?总待在空调房里也不是个办法:吹久了身子酸骨头疼,闲坐久了又闷得慌。倒不如出门去,找片树荫儿透透气。
一日,我骑上电动车向黄河岸边走去,还没钻进树林,就听见热闹的声响——大片林子里早挤满了人,活脱脱一个“乘凉乐园”。戏班子搭起简易戏台,胡琴一挑,吱呀作响,老生的唱腔裹着泥土味,顺着树影儿悠悠荡开;便携桌上摆着象棋、麻将、扑克,甩牌声混着嬉笑声,此起彼伏;有人躺在吊床里晃悠,枕着风打盹,吊床绳勒得树木轻轻颤;孩童们追着蜻蜓、蝴蝶跑,凉鞋踩过草叶的沙沙声,混着清脆的笑声,比蝉鸣更添几分活气;老人们坐在小马扎上唠嗑,说谁家的玉米长势好,准能高产;录音机里的梆子戏和手机里短视频的笑声交织在一起,成了独有的“乘凉文化”。
可往前数些年,这“乘凉文化”是稀罕物,乘凉甚至可算得上一种奢侈品。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——那会儿的农民哪有这闲工夫?就说我家,四口人守着六亩多地,我在县城上班,孩子们上学,家里的农活全靠老伴扛着。收完麦子种上秋庄稼,出土的禾苗急着灭茬、除草、间苗、松土,我总在下班后骑上自行车赶回家搭把手。稍慢一步,碰上连阴雨,地里的活儿来不及收拾,杂草就疯长,秋粮准得减产。夏天的地,除了浇水施肥,还得锄三遍:头遍灭茬,二遍除草、间苗,到第三遍松土后“挂锄钩”,才算能喘口气。从这时候到收秋,才能勉强挤出点空档。
如今不一样了。地里的变化大着呢:拖拉机、播种机、收割机成了主力,无人机嗡嗡掠过,打药、施肥一趟子办妥;秸秆还田省去清运的麻烦,复合肥养得土地肥实;连间苗都省了——玉米株距从过去的一尺多缩到三四寸,亩产反倒稳超千斤;灭草、治虫、抑长、增产,一套“庄稼管理套餐”全解决。哪还用得着一遍遍地锄地?
田里的活计减了大半,青壮年揣着手艺进城务工,老人们守着几亩田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倒也落得自在。夏日的风里,乘凉不再是奢望,成了日子里的寻常滋味。你再看那黄河岸边的树林里,戏照唱,嗑照唠,手机照刷,孩子们照闹,日子就这么在凉爽里慢慢酿成了独有的“乘凉文化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