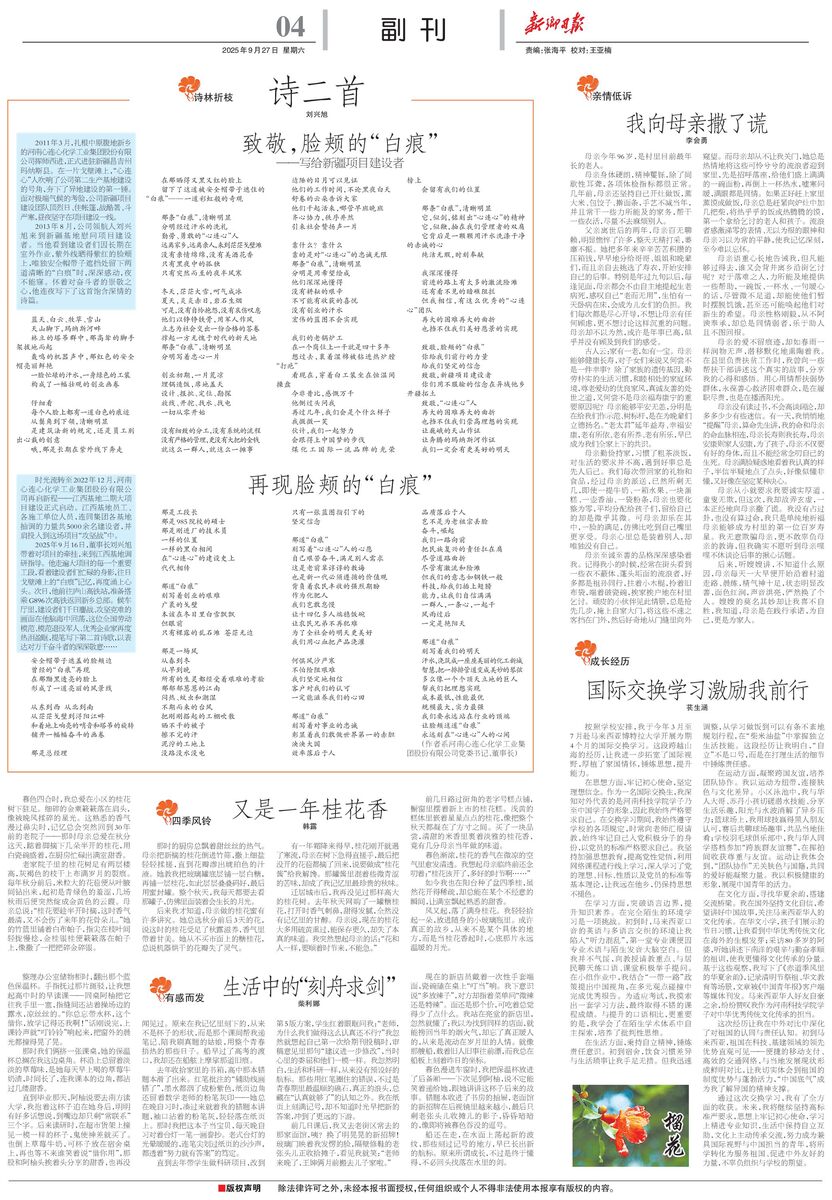生活中的“刻舟求剑”
发布时间: 信息来源:
柴利娜
整理办公室储物柜时,翻出那个蓝色保温杯。手指抚过那片斑驳,让我想起高中时的早读课——同桌阿柚把它往我手里一塞,指缝间还沾着操场边的露水,凉丝丝的。“你总忘带水杯,这个借你,放学记得还我啊!”话刚说完,上课铃声就“叮铃铃”响起来,把窗外的晨光都撞得晃了晃。
那时我们俩挤一张课桌,她的保温杯总搁在我这边桌角。杯沿上总留着淡淡的草莓味,是她每天早上喝的草莓牛奶渍,时间长了,连我课本的边角,都沾过几缕甜香。
直到毕业那天,阿柚说要去南方读大学,我抱着这杯子追在她身后,明明有好多话想说,到嘴边却只剩“常联系”三个字。后来读研时,在超市货架上撞见一模一样的杯子,鬼使神差就买了。也倒上草莓牛奶,可杯子放在宿舍桌上,再也等不来谁笑着说“借你用”,那股和阿柚头挨着头分享的甜香,也再没闻见过。原来在我记忆里刻下的,从来不是杯子的形状,而是那个课间帮我递笔记、陪我刷真题的姑娘,用整个青春捂热的那些日子。船早过了高考的渡口,我却还在船舷上摩挲那道旧痕。
去年收拾家里的书箱,高中那本错题本滑了出来。红笔批注的“辅助线画错了”,墨水都洇了成粉紫色,纸页边角还留着数学老师的粉笔灰印——她总在晚自习时,凑过来就着我的错题本讲题,袖口沾着的粉笔灰,轻轻落在纸页上。那时我把这本子当宝贝,每天晚自习对着台灯一笔一画誊抄。老式台灯的光晕暖暖的,连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,都透着“努力就有答案”的笃定。
直到去年带学生做科研项目,改到第5版方案,学生红着眼眶问我:“老师,为什么我们做得这么认真还不行?”我忽然就想起自己第一次给期刊投稿时,审稿意见里那句“建议进一步修改”,当时心里的委屈和他们一模一样。我忽然明白,生活和科研一样,从来没有预设好的航标。那些用红笔圈住的错误,不过是青春期里最温顺的礁石,真正的浪头,总藏在“认真就够了”的认知之外。我在纸页上刻满记号,却不知道时光早把新的答案,冲到了更远的下游。
前几日课后,我又去老街区常去的那家面馆,咦?换了明晃晃的新招牌!玻璃门映着我发愣的脸,隔壁修鞋的老张头儿正收拾摊子,看见我就笑:“老师来晚了,王婶俩月前搬去儿子家啦。”
现在的新店员戴着一次性手套端面,瓷碗磕在桌上“叮当”响。我下意识说“多放辣子”,对方却指着菜单问“微辣还是特辣”。面还是那个价,可吃着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我站在亮堂的新店里,忽然就懂了:我以为找到同样的店面,就能捞回当年的烟火气,却忘了真正暖人的,从来是流动在岁月里的人情。就像那艘船,载着旧人旧事往前漂,而我总在船板上刻着昨日的坐标。
暮色漫进车窗时,我把保温杯放进了后备厢——下次见到阿柚,说不定能笑着递给她,跟她讲讲这杯子后来的故事。错题本收进了书房的抽屉,老面馆的新招牌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,最后只剩老张头儿收摊儿的影子,昏昏暗暗的,像即将被暮色吞没的逗号。
船还在走,在水面上荡起新的波纹,那些刻过记号的地方,早已长出新的航标。原来所谓成长,不过是终于懂得,不必回头找落在水里的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