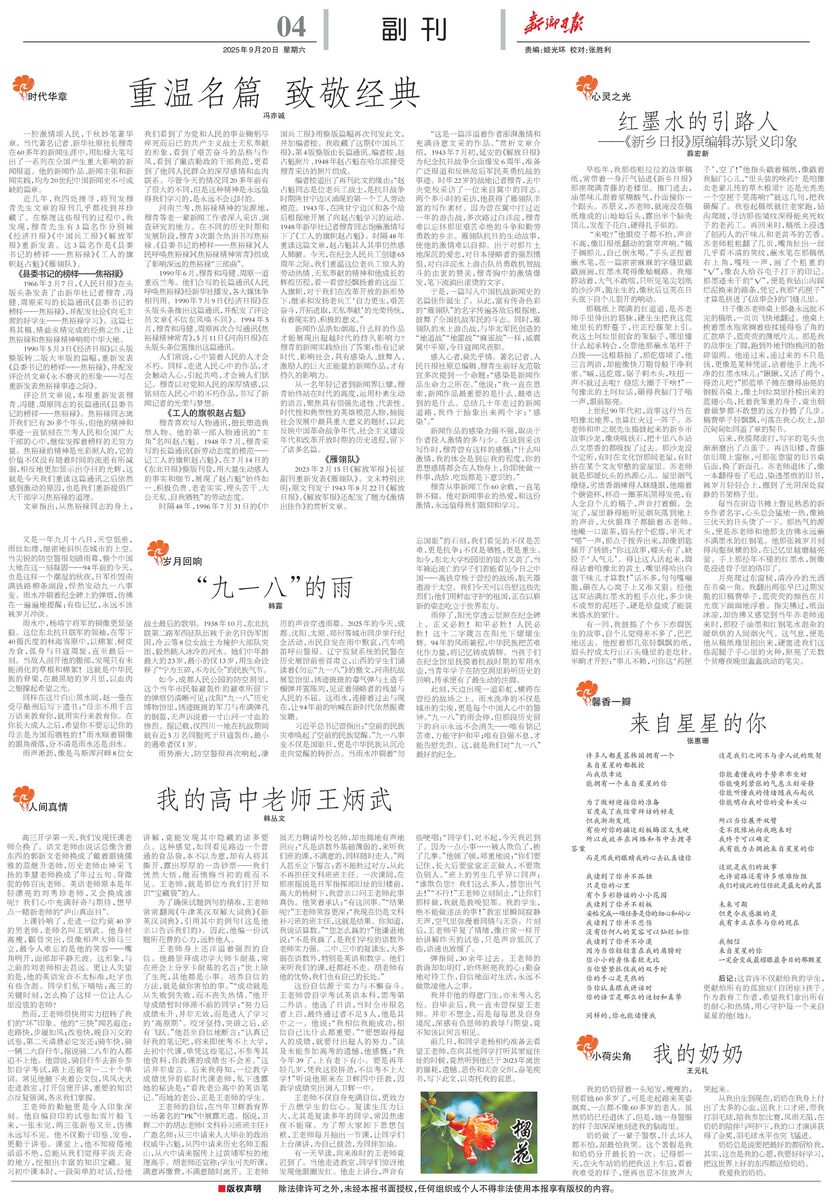红墨水的引路人
发布时间: 信息来源:
——《新乡日报》原编辑苏景义印象
薛宏新
早些年,我那些粗拉拉的故事稿纸,常带着一身汗气钻进《新乡日报》那座爬满青藤的老楼里。推门进去,油墨味儿混着浆糊酸气,扑面撞你一个跟头。苏景义,苏老师,就淹没在稿纸堆成的山坳坳后头,露出半个脑壳顶儿,发茬子花白,硬得扎手似的。
“来啦?”他眼皮子都不抬,声音不高,像旧报纸翻动的窸窣声响。“稿子搁那儿,自己倒水喝。”手头正捏着蘸水笔,在一篇密密麻麻的字缝里戳戳画画,红墨水爬得像蚰蜒路。我缩脖站着,大气不敢喘,只听见笔尖划纸的沙沙声,脆生生的,像秋后豆荚在日头底下自个儿裂开的响动。
那稿纸上爬满的红道道,是苏老师手里伸出的筋脉,硬生生把我这荒地里长的野蔓子,往正经藤架上引。我这土坷垃里刨食的笨脑子,哪里懂什么起承转合,全靠他那蘸水笔杆子点拨——这根筋抽了,那疙瘩堵了,他三言两语,却能像快刀剔骨般干净利索。“嘁,这疙瘩,锯子剌木头,吱扭一声不就过去啦?绕恁大圈子干啥!”一句豫北的土坷垃话,砸得我脑门子嗡一声,眼前豁亮。
上世纪90年代初,故事这行当在咱豫北地界,也算红火过一阵子。苏老师和申之珉先生捣鼓起来的新乡市故事沙龙,像块吸铁石,把十里八乡沾点文墨香的都吸拢了过去。那沙龙没个定所,有时在文化馆那间老屋,有时挤在某个文友窄憋的堂屋里。苏老师就是那暖炕头的热源心儿。屋里烟气缭绕,劣质香烟辣得人眯缝眼,他端着个搪瓷杯,杯沿一圈茶垢黑得发亮,有人念自个儿的稿子,声音打着颤。念完了,屋里静得能听见烟灰落到地上的声音,大伙眼珠子都瞄着苏老师。他嘬一口浓茶,眉头拧个疙瘩,半天才“嗯”一声,那点子拨弄出来,却像钥匙捅开了锈锁:“你这故事,噱头有了,缺股子‘人气儿’。得让这人活起来,脚得沾着咱豫北的黄土,嘴里得哈出白薯干味儿才算数!”话不多,句句嘎嘣脆,砸在人心窝子上又准又狠。经他这双沾满红墨水的粗手点化,多少块不成型的泥坯子,硬是给盘成了能装米盛水的家什。
有一回,我鼓捣了个乡下赤脚医生的故事,自个儿觉得差不多了,巴巴地送去。他捏着那几张轻飘飘的纸,眉头拧成太行山石头缝里的老圪针。半晌才开腔:“事儿不赖,可你这‘药匣子’,空了!”他指头戳着稿纸,像戳着我脑门心儿,“里头装的啥药?是咱豫北老辈儿传的草木根须?还是光秃秃一个空匣子晃荡响?”就这几句,把我砸醒了。我卷起稿纸就往老家跑,钻沟爬坡,寻访那些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的老药工。再回来时,稿纸上浸透了刨药人的汗味儿和老黄芩的苦香。苏老师粗粗翻了几页,嘴角扯出一丝几乎看不清的笑纹,蘸水笔在那稿纸右上角,嘎吱一声,画了个粗重的“√”,像农人给谷屯子打下的印记。那墨迹未干的“√”,便是我钻山沟踩烂泥换来的路条,凭它,我那“药匣子”才算是挤进了《故事会》的门缝儿里。
日子像苏老师桌上那叠永远批不完的稿纸,一页页飞快地翻过。他桌上挨着墨水瓶常搁着些揉搓得卷了角的汇款单子,蓝荧荧的薄纸片儿。那是我的故事生了脚,跑到外地刊物换回的散碎银两。他递过来,递过来的不只是钱,更像是某种凭证,沾着他手上洗不净的红墨水味儿:“瞅瞅,又活了两个,得劲儿吧?”那蓝单子摊在磨得油亮的钢板书桌上,像土坷垃窝里扑棱出来的蓝翅小鸟,托着我笨重的身子,竟也朝着做梦都不敢想的远方扑腾了几步。稿费单子轻飘飘,可落在我心坎上,却沉甸甸如同盖了章的契书。
后来,我摸爬滚打,写字的笔头也渐渐磨出了点茧子。再访旧楼,青藤依旧爬上窗框,可那张靠窗的旧书桌后面,换了新面孔。苏老师退休了,像一本翻得卷了毛边、染透墨痕的旧书,被岁月轻轻合上,挪到了光阴深处寂静的书架格子里。
每当在街边书摊上瞥见熟悉的新乡作者名字,心头总会猛地一热,像被三伏天的日头烫了一下。那热气的源头,便是苏老师和他那支仿佛永远蘸不满墨水的红钢笔。他那张被岁月刻得沟壑纵横的脸,在记忆里越磨越亮堂。手上那经年不褪的红墨水,倒像是浸进骨子里的烙印了。
月亮爬过东窗棂,清泠泠的光洒在书桌一角。我翻出两张早已过期发脆的旧稿费单子,蓝荧荧的颜色在月光底下幽幽地浮着。指尖拂过,纸面冰凉,却仿佛又感觉到当年苏老师递来时,那股子油墨和红钢笔水混杂的暖烘烘的人间烟火气。这气息,便是他从稿纸堆里刨出来,硬塞进我们这些泥腿子手心里的火种,照亮了无数个贫瘠夜晚里蠢蠢欲动的笔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