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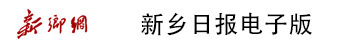


雪
|
王保银 (辉县市)
一到冬天,我总是会想起雪,这大概和多年前的一场雪有关。那时我的心也如这雪天一样苍凉迷蒙,因为一件事而苦恼。那时,我已二次高考落榜,这种失败的打击让我心如死灰,整个人像垮掉一样。
突然间就喜从天降了,村里要招聘教师。闻听消息,我如打了鸡血般兴奋,于是兴冲冲地报了名,一切如愿以偿。但我很快被新的愤怒震慑,我考上了却被告知不被录用,不录用的理由无耻而荒唐,竟然还是因为我糟糕的身体。
做出这个近乎残酷决定的,说是大队“两委”班子的一次集体会议,其实是一个人从中作梗,才遭致我人生的又一场“滑铁卢”,我顿时心生愤怒和恼恨。
我是一个天性按捺不住的人,我迅及抓起我家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“飞鹰”,一纵身就如射箭般蹿出那座破旧院落。我要上家找他去,我倒要问个青红皂白,他究竟和我有冤还是有仇,为什么要做出这事,给我带血的伤口撒盐,难道我人生的痛苦磨难还不够吗?
我被心底一股邪火挟持着,穿过脏乱的街道,向他的家里奔去。他家在村南街住,从街中间南边一条很深的胡同一直走到头,左手边那个露天门楼进去就是他的家。
风里突然有冷凉的东西朝头上落,仰头看天,雪悄然下起来了,起初是坚硬的颗粒落下来,在空气里摩擦出沙沙的声响,硌得脸有些疼,且越下越急,风也越发凛冽。不一会儿,坚硬的颗粒变成了雪花,大朵小朵的,围绕着我旋转扑打。
那条小巷怎么没出现呢?我明明是朝这儿走来的呀!我心中被积淤已久的怒气鼓胀着,我恨透了这个人,今天我一定要找到他,而现在我气急得一时竟摸不着北了。
就在这时,我发现这空寂无人的街道对面走来一个人,飞雪模糊了我的视线,等走近了,我才看清是董婶。她在北街住,这里是南街,这么恶劣的天气,她出来干啥?
不等我开口问,她先说话了:“恁冷的天出门,有啥急事?”
我好像含糊地应了一声。
喊董婶是街坊称谓,她是村上的妇女干部。她笑笑,不等我回答又说:“我想起来了,知道你找谁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?”我一时被她的话弄蒙了。
不等我反应过来,她又接着说:“我还知道你为啥事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可不是,她是村委班子成员,她一定参加了那个事关我命运的会议决定。
我吃惊地看着她,即使她真的知道,我也不能如实相告。
她一定看出了我的内心正被炽烈的怒火烘烤着。但她显然是顾及我的面子而没把事捅开。她很淡然地说:“你回吧。”
我说:“我不回,你既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我倒要问清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?”
她并没接着我的话往下说,而是转移话题:“现在很冷吧?”
我不耐烦地回答她:“下雪天能不冷?”
她好像没听出我的厌烦,继续说:“这风总会停下来,这雪也不过就是一阵。风一停,雪一消,太阳一出来,这天就不冷了。”
这句话,一下子把我定在冰冷的雪地里,像凝固似的一动不动了。
她说完那句话,又对我笑笑,转身走了。
我觉着那笑里有一层深意,特别是她的那句话,不知怎的一下子触动了我。那个声音听来意味深长,很明显地蕴含着什么,像一把尖刀飞出,嗖的一声把这漫天飞雪划出一道口子,在寒冷的空气里迸射开来。似乎就在那一刻,我忽然对自己此行的目的和意义产生了疑惑。
雪还在下,风势助阵,雪越发急速而强劲,屋顶和地面已是厚厚一层,四周的街道和房屋笼罩在一片暗淡迷茫的白里,让我一时产生了幻觉,不知身在何处。
我不由得在胡同口站着了,任这雪潇潇地下,任这雪上下包围着我,任这雪在我的头顶覆盖,在我的肩背上疾落,而原先的一腔怒气却在这一片银白里融化了。
董婶的话似这风搅雪在我的心头漫卷。不知怎的,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冬日午后,此刻间却全然没有了来时的那种激愤之情。我在他家的胡同口平静地站了一会儿,踱着步,一圈又一圈,在雪地里踱成一个大大的圆圈,不一会儿雪又覆盖了一切。我不由仰头看天,雪落在我的脸上,迷蒙了我的双眼,我的大脑一下子清亮如水,一股暖意在全身发散开来。我又回转身,骑上我那辆破车子,迎着风雪又沿着街中的大路走去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