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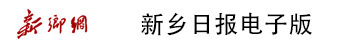


老家门前那口井
张文慧 (新乡市)
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。闲暇之余,总还会想起老家门前那口老井。
老井不大,口径有一米多宽,深约两丈有余,井口的岩石被岁月的脚印打磨得锃光瓦亮。从井口俯瞰,井壁的石缝里长满了毛绒绒的青苔,井水是蓝褐色的。我投下一粒石子,身影随着清澈的井水荡漾,水面也会泛起层层涟漪。
我趴在井沿上,掬起一捧井水喝上一口,冰凉甘甜,清爽酣畅,好似一杯玉液琼浆,让久别家乡的我有一种渴望的乡愁。
这口老井像一位慈祥的老人,年年岁岁、日日夜夜,一直守望着我们的村庄,滋养着全村300多口人的生命。
我的老家坐落在太行山南麓,是黄河北岸的一个小村,与众多的豫北平原乡村没啥两样,房是蓝砖、土墙、灰瓦、四合院,树有榆树、杨树、桐树、槐树、石榴树……间杂在房前屋后空地上、左邻右舍院落里。村的中间贯穿着一条东西长街,约二百来米,四十多户人家,齐整地排居在街道两旁,倒也显得整洁小巧、规整有序。
村子北边,有一个高高隆起的大土丘,原是一座寺庙留下来的遗址,寺名叫“清凉寺”,始建于唐朝,明嘉靖四十一年、清康熙十九年河内府进行了修缮。可惜,偌大的寺庙毁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的战火。
听老人们说,当年寺庙香火旺盛,门庭若市,方圆百里的善男信女,怀揣执念和梦想,每天早早赶来进香。逢年过节则是另一番景象,络绎不绝的人们涌动在寺庙院落里,直到月明星稀,人们才依依散去,只留下微风中忽明忽暗的香火。
老家的房子,坐落在街道中间偏西方向,距离寺庙不算很远。那口老井就在我家的门前,村里人挑水来来往往,多集中在两个时辰,早晨和傍晚的饭前饭后。每天这个时候,人们便挑着水桶、拿着盆盆罐罐来打水,人多时还得排队,于是水井旁就成了乡里乡亲见面说话拉家常的地点。有的聊东家长西家短;有的说村里村外逸闻趣事;有的说起“外面的世界”,滔滔不绝,眼里放着光,面部表情夸张,显示着自己见过世面的自豪和优越。
已经打上水的人,见到这热闹的场面,也不着急回家,站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听着。有经验有力气的人总会凭着技巧,把水桶打得满满的。他们打水时动作娴熟,身手敏捷,不用眼睛盯着,单是用手三摆两摆,扑通一声,整个水桶就会来个底朝天,然后桶沉到水里,顺势轻松地提上来满满一桶水。
不常打水的人刚开始打水,常常将桶放在井里,小心翼翼地摆来摆去,就是打不到水。有时,一不小心,摆幅过大桶就会脱钩,水桶在井里灌满水后,就会沉到井底。这时,还得请村上有经验的人,将沉落井底的桶用“盲钩”打捞上来。我也经常在打水时脱钩,遭到大人的训斥,甚至还会挨上几个轻轻的巴掌。
村里人吃饭时喜欢聚堆,井旁边空地儿就成了饭场。端着饭碗早出来的人,就会站着或蹲在井台周边最好最高的位置,显示着位置的优势。尤其是夏天,要么头顶火辣辣的太阳,要么浓雾锁天,气候闷热。年轻野性足的人,干脆面朝老井坐在井沿上,两条腿腾空下垂到井中,任由井底的凉气顺着腿慢慢浸润全身,那个凉爽劲儿呀,真是美滋滋的!当然,吃饭的那会儿,自然又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,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谈天说地、吹牛聊天、说着段子。
老井有段不寻常的来历。
那个时代,我爷爷还年轻,村里吃水浇地需到清凉寺背后那条小河挑水,小河属于沁河的一条支流,潺潺的溪流从太行山的石缝中流出,清澈甘甜,鱼肥草丰。但小河离村里较远,村里人便合计着在村里打一口井,方便乡亲们就近担水。但把井打在哪里,成了难题。村上的街道只有两米多宽,家家户户的房子沿街而建。房屋墙根儿离路边最宽的地方也才两米多,井打在谁家的房前屋后,都会影响房子的根基,因而,谁都不情愿把水井打在自家的门前。
一个月过去了,两个月过去了,村里人还没商量出个结果。这天,村里众人又在商议,有人提出:“在景春家门前打井吧!” 张景春是我的爷爷,村里人的理由是:张景春家位于村子中心位置,东西两头的人打起水来都方便。
爷爷听了村里人讲的理由,觉得有点儿牵强附会,但他为人忠厚善良、淳朴心实,一时没有说话。村干部见爷爷没有反对,就顺水推舟,打井的事儿算是定了下来。
回到家里,爷爷坐在自制的小板凳上,吧嗒吧嗒抽着旱烟,沉默不语。心想:打井是为了全村群众好,打在咱门前,应该!但是,真挖在自己的房前,这些年来全家人攒着钱财力气刚盖好的房子,一旦根基塌陷、墙体松动,整个房子就会倒塌,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这可是个天大的事情啊!何况,自家也不是在村子的最中间,如果论村两头的人打水方便,有几家比我们家的位置更合适。
寻思来寻思去,就是想不出一个理由来,按照爷爷的脾气秉性,自己家的家规家风,也不会去争辩推翻。那晚,爷爷在院落里抽着烟坐到深夜,地上散落了一堆厚厚的烟灰。
就这样,村里开始了挖井。
挖井那天,村里的头人领着街坊邻里,上了香、放了炮,还给俺家送来了一小筐鸡蛋,算是给爷爷的一些补偿,爷爷原本憋在心里的话,又被这筐鸡蛋给堵了回去。
半个月后,全村人翘首盼望的井,终于见水了。
傍晚,正当劳累一天的人们准备收工时,意外发生了,从井底提泥土的绳子突然断了,装满稀泥的土筐重重地掉落下来,正好砸到在井底挖泥掏土的爷爷头上。
“不好,出事了……”
乡亲们把爷爷从井底泥水中捞上地面时,爷爷已经没有了呼吸,心脏停止了跳动。
后来,水井终于挖好了,哗哗的井水喷涌而出,井水清澈甘甜,村民掬起一捧,一饮而尽,咂咂嘴直喊:“真甜!”但是这滋养着世世代代村人的井水,爷爷却没能喝上,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……
到了我父亲那辈,为了乡亲们打水方便,父亲先是买了水泥对井的周边进行了衬砌,后来又在井的上方装上了手摇的轱辘。这样,打一桶水可以节省很多力气,村里的老人、妇女、大点儿的孩子也都能来打水了。
我记事时,看到老家的祖房墙上裂开了一道缝隙,裂缝从墙根攀爬向上,一直到了房檐,弯弯曲曲的活像一条龙,着实恐慌吓人。
我走出小村工作很多年后,有一年回到老家过年,门前的那口老井还在,水井黑咕隆咚,深不见底,已没有了水,成了一口废弃的枯井,乡亲们早已用上了自来水。
此后,我每年回老家,都会围绕老井转上几圈,并伫立在井旁,任由思绪回到遥远的过去。
其实,一口老井,早已成为一段乡村历史,它承载着乡愁的记忆、根脉的传承、生活的过往;一口老井,是一个村庄的风情和故事,早已镌刻在大地乡村的血脉里;一口老井,是一个乡村游子的思念和惦记,呼唤着远走他乡的人们家的方向、根的灵魂。
乡村老井,是一个村庄永远磨洗不掉的胎记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