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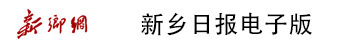


从三次大水灾吃饭谈起
周书淮 (卫辉市)
我特别喜欢吃大米饭,大米是个馋食,它最易和大肉搭配。常言说,“大米干饭肉浇头,越吃越香口流油。”这些年真饱了我的口福啦,三天两头大米干饭肉浇头。一个中午,我又端着雪白的大米饭,上边浇着透红剔亮的方块肉。刚坐在小区广场上,几个到小区搞宣教的年轻人看着我吃得蛮过瘾,哈哈一笑,“大爷,看着您这饭碗真不像刚受过大水灾啊!”我口中边嚼着肉,边微微一笑俏皮地回答:“这次遭受这么大的水灾后,我想可要把我这吃大米肉浇头的瘾给饿掉了。谁知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,小区办事处很快把成袋的大米白面、成桶的食油还有救灾款送到了家门,这是托共产党的福啊!”年轻人趁势接着问:“大爷,您这把高寿,经历多,过去要遭这么大水灾怎么样?”这一问,击中了我心头的火花,满肚子的苦辣像溃堤决坝的江水一样喷涌而出。
我今年八十五岁,这一生共经历了三次大水灾。第一次是1944年8月,我刚刚七岁。我们全家四口生活在浚县农村。8月中旬暴雨铺天盖地一连下了五天六夜,到处一片汪洋,不少家户房倒屋塌。当时父亲在外谋生,我同母亲、哥哥蜷缩在两间遍地漏雨的破房里,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被砸个稀巴烂。当时吃的别说米面,就连糠菜也一光二净,已经几顿没开锅了。妈妈眼看俺兄弟俩饿得抬不起头了,突然指指院里被风雨刮落的烂枣。我和哥哥二话不说,冒雨跑到院里拾起烂枣,也不管泥水虫蛀大口吃开了。妈妈看着忙说:“生的吃多了拉肚子,煮熟吃吧。”煮熟,谈何容易?一者无锅,二者烧火的秸秆杂草全泡在水里。想来想去,想起床底下还放几捆准备纳锅盖用的高粱箭。俺兄弟俩拿出来,趁着墙角用两块儿半截砖架起一只小铁筒开始煮枣。可是我俩根本等不上熟,一把把捞出狼吞虎咽,半小筒枣片刻一扫而光。就这样,一连几天全靠煮烂枣填肚子。
第二次大水灾是1963年8月上旬,暴雨连下几天几夜,那时我已在汲县(今卫辉市)参加工作成家立业。当时国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加之罕见的大水灾,真是雪上加霜。那时吃粮是低标准供应,多半是红薯干、红薯面之类。可就这些东西,也由于城里城外成了“水乡泽国”运不进来,供应不上。后来政府专派民航飞机向全县几处重灾区投放大饼、馒头、炒黄豆等食物。先后有五六架飞机投了不少食物,但对城区几万张嘴来说仍是杯水车薪,我家连个饼馍影子也没见到。几天后,北阁门外大水稍退了一些,政府用船从外地调进一部分红薯干救济灾民。我高高兴兴地到赈灾点领了十多斤。谁知乐极生悲,行至家门口时,因路滑摔倒,口袋震裂,红薯干全部撒在泥里,又恰遇风吹,红薯干和泥水混得一塌糊涂。我不顾疼痛爬起来,赶忙将红薯干连泥带土撮回家中,虽经再三挑拣清洗,吃起来有些艮牙,可还是感觉又香又甜,吃了还想吃。日子一直熬了几个月,进入冬季,天气冷,肚里空,实在难挺。无奈,我跟随不少人一样,收拣些旧衣服,趁星期天起早搭黑扒火车到一百多里外的汤阴换些红萝卜,回来搭配供应的红薯熬日月。“红薯汤、红薯馍,离了红薯不能活”就是那时叫响的。细想想,红薯还真是好东西,那时救人命,当今吃稀罕。
最后我再说说这次大水灾,刚一开口,身边的年轻人异口同声:“大爷,不用再细说啦,这次大水灾咱们感同身受,共同受助得益。就像您开初谈的,这雪白的大米、成袋的白面,是党和政府一次又一次给咱送到家的。放心吧,您老人家这吃大米干饭肉浇头的瘾不会饿掉了。”听了年轻人的话,我顿时心血来潮,脱口而出:“同样大水淹,吃饭不一般,不忘党的恩,饮水应思源。”话毕,大家报以热烈掌声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