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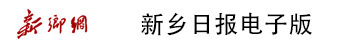


爆米花香
张建广 (辉县市)
冬天的夜晚来得早。
小区门口,路边空地上,鼓风机“呼呼”地给小铁炉鼓着劲儿,炉焰跳着欢快的鬼步舞,晚霞般映照着人们的脸。男人五六十岁,蓝衣灰裤黑布鞋,坐一小马扎,专注地摇着爆米花机。爆米花机像只翻滚的小海豹,火舌热情地舔着它灰黑的肚皮。
火候到了。男人关掉鼓风机,起身拎转爆米花机,把机头摁进布袋的口里,左手抓紧摇手,右手用钢管套住大弯头,右脚朝着爆米花机的脖口一踹,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一团白雾腾起,男人被吞没其中。一丈多长的布袋胀起来,热气腾腾,里边爆满了玉米花,扑鼻的香。男人往一端收拢着布袋,爆米花的主顾早掀掉压袋脚的石块儿,玉米花“哗哗”地泻满大笸箩。
通常,男人身边坐着娘,满头银发,安静而慈祥。这时,老人缓缓起身,用颤巍巍的双手撑开塑料袋,两袋刚好装满;左一袋,右一袋,爆米花的主顾满载而归。爆米花机大口朝上竖着,炮筒一样威风凛凛。男人操起搪瓷大碗,伸进小编织袋,搲满,抹平,金灿灿的玉米粒“哗哗”地倒进爆米花机的肚子里,盖盖儿,螺紧,支回炉架,添炭,开风机……动作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。
十年前,男人在县城给儿子买了婚房,小两口三年生俩娃,然后丢下孩子一起下广州淘金去了,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。孙子一天天长大,小两口打来电话,执意让俩孩子去县城上幼儿园。他干脆流转了农田,出租了猪场,带着妻子和老娘住进了县城。妻子负责照顾娘,接送孙子,自己在一家洗浴中心干起了搓澡工,周五歇一天。娘老了,在城里呆不惯,一直絮叨着回农村一人住。妻子说,小区里有花鸟虫鱼,环境多好;娘说,再好也没有农村好。娘吃饭少了,说话也少了,整天靠在沙发上“睡电视”——电视一开就睡,一关就醒。
餐桌前,娘忽然说想吃爆米花。他的心潮湿了,想起了爹。
爹一生勤俭,起早贪黒,任劳任怨。冬天农活少,爹就推着板车游村串巷地爆米花。冬夜漫漫,爹迎风冒雪摇月光;娘帮着爹,收钱倒水递干粮。爹用一锅一锅爆米花攒下的钱,翻盖了房子,买了四轮拖拉机,还供他上了高中,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比炉火还旺,村里人都夸爹是“能一锅”。可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那年,爹得了食道癌。爹怕花钱,更怕耽误儿子的学业,坚决不住院不手术。娘说,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去看病。手术做完了,药是一堆一堆地吃,爹却一天一天地瘦下去。当村里人都忙着收麦打场时,爹走了,天塌了。从此,家境一落千丈。娘用柔弱的身体,支撑起了这个不完整的家。
……
爹生前用过的爆米花机,娘不让扔也不让卖。他从老家带过来,修理改造后说:“娘,我载着你去爆米花吧。”娘笑了。
三年来,每周五歇工,他都要载着娘去小区门口爆米花。娘的听力不好,可每一次“嘭”的一声,她都听得见。娘看着他忙,也来帮忙。他见娘高兴,心里也高兴。小区里的人都说:“大娘啊,您儿子爆的米花就是香,跟别家的味道不一样。”
娘不再说回老家了,每天都问他:“今儿个星期几了?”
一场寒流袭来,东北风肆虐了一天一夜,气温骤降。天空阴云密布,人们都盼着能捂场大雪,可老天偏不。老人咳嗽了,大人感冒了,孩子发烧了,医院的走廊里也挤满了病床。这个周末,小区门口冷冷清清,连只路过的猫狗也没有。有人拎着玉米出来了,路灯泛着白光,空地上干干净净,压袋脚的石块儿静静地靠在墙脚,却看不到他和娘。两周,三周,人们焦急而无奈。有人说,他一直陪娘在医院,老人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。
吃不上他爆的米花,日子是那么的索然无味。
腊八节过后,树枝上扯起了花灯,灯带绕成的大大的“福”字在景观石上闪闪发亮。
“嘭”——小区门口传来一声巨响。
“今天是周几?”
“周五。”
“快,快,快,爆米花的来了。”
有人率先冲出楼梯,空气中正弥漫着诱人的米花香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