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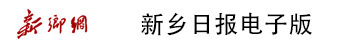


草女人、舞女人
冯霜凌 (辉县市)
村庄的土里到处长着草。
田畈地头,旮旮旯旯,沟沟壑壑。春风一暖,小草迫不及待地从泥土里拱出来,露出绿茸茸的芽儿;春雨再一润,大地刹那间热闹起来:青绿色的、墨绿色的、灰青色的……各种各样的草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。你走在田埂上,它拽着你的眼;你蹲在沟渠边,它毛茸茸地盯着你的脸;你把它薅回家,扔进猪圈里,喂进猪肚里,猪一拉,猪粪又上进了庄稼地里。来年,它又得意洋洋地长出来。草和庄稼人扯上了割不断的亲情:草看到人近,人看到草亲。
田里刨食的年月,家家户户都要养一两头猪。别小看这呆头呆脑的猪,那可是庄稼人的钱袋子、命根子,一大家子的吃喝用度可是指望它哩。只是人还吃不饱,哪来的多余粮食喂猪?可活人还能让尿憋死?闹饥荒的年月,人都啃的树皮,吃的野菜,猪又有啥吃不得的?于是乎,那些茂茂盛盛的草就成了猪的主食。主妇们把薅来的野草剁碎,搁点麸皮或刷锅、刷碗的潲水一搅拌,就成了猪们的盛宴。
大集体的年月,伸手掐腰的队长一吆喝:“妇女们先下晌,回家做饭去!”像得了将令一样,不管是在地里锄地的还是打坷垃的妇女们,赶紧收拾锄把或抓钩,顾不得回家,背起地头的萝头筐,先去给猪打筐猪草。猪比人金贵,猪也饿得“嗷嗷”直叫哩。
妇女们三三两两,你在沟渠边,我在田头下,马婶薅把灰灰菜,三婶拔的猪苗菜,顾不得蹲下,低着头,弯着腰,撅起裤上打着补丁的屁股,左右手开弓,满把手地薅着。一不小心,手被草划破了,血乎乎的,主妇们用嘴一吸,随手抓把细土一捺算是完事。继续薅,赶紧薅,一家老小都还等着她回去擀面条做饭吃呢。转眼间,箩筐满了,大娘大婶们用手拨拉一下眉梢的汗,用锄把或者抓钩把儿扛着箩筐心满意足地回家。草先扔进猪圈里几把,让猪也先压压饥。主妇们“啰啰啰”地叫着,猪“哼哼哼”欢叫着奔过去。主妇们打量几眼又长了一点膘的猪,喜上眉梢,这才急急忙忙地去烧火做饭。
春夏秋冬,日日月月,庄稼女人的手都是青黑青黑的,那是草染的颜色。她们的手似老枣树皮,开着缝、裂着纹,摸上去,硬邦邦、涩拉拉,又像刺猬身上的刺儿,扎得人生疼生疼。但她们照样没心没肺地开着粗野的玩笑,嘻嘻哈哈,打打闹闹。小时候不懂事,暗地里把这些女人称为“大屁股女人”。真的,她们实在太像“大屁股草”了。村里到处都长着“大屁股草”,这种草坐摊儿大,叶茎肥厚,但极不好薅,你用尽吃奶的力气,累得你人仰马翻,它却纹丝不动,除了满手的汁液和深深的勒痕外,别无它获。这种菜必须用镰刀割。只是这边才割罢,那边就又欢天喜地长出来,生命力极强,像极了村里的女人:不妖媚,不矫揉,不做作,皮皮实实,泼泼辣辣过着自己的时光。
上一辈的女人就这样一天一天熬过来了,下一辈的女人还得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。小小年纪,十来岁的模样,挎着竹篮,三五成群、四五一堆跑散在田野上。
不过是早春二月间,麦苗还没有完全返青,妈就拿出几个破竹篮:“去,你们几个放学后去薅猪菜,不薅满别回家吃饭。”大米捞饭棵儿、忘不了籽棵儿、双色草等,刚从地里拱出小嫩芽儿。我们蹲在麦地里,不是薅,是用指甲挖,草还太小,指甲挖裂了,指甲挖秃了,一筐筐一筐筐的草薅回了家。春天有大米捞饭棵儿、松菌草、水草叶;初夏有猪苗菜、灰灰菜、鬼鬼圪针;秋有齿牙菜、鸡蛋棵儿;冬天,我们就捡起落地一层的桐树叶,一麻袋一麻袋扛回家,揉碎,煮熟,喂猪。
七八岁的时候,二姐、三姐领着我,辨认哪是大米捞饭棵儿、哪是忘不了籽棵儿。等麦子快熟时,草的果子也熟了。二姐小心地从大米捞饭棵儿上摘下几个小果子,剥开,里面果然藏着好多细小、洁白的米粒,尝一口,嗯,有点清香。
十来岁的时候,我领着两个妹妹,教她们哪是齿牙菜、哪是布兜兜。小妹妹极馋,光记住了布兜兜。布兜兜是长在坡上的一种草,灰青色的,结的果子细长,极像布袋。玉蜀黍成熟的季节,它也熟了,果子可以连皮吃,一棵秧上结几个布兜兜。布兜兜的味道很特别,苦里透着香。
乡村女孩儿什么都不知道,却知道大地上很多草的名字,我们还知道哪些草喜欢潮湿,长在沟渠边;哪些草喜欢松散的沙土地,长在花生地里。我们熟知草的习性,一如熟悉自己朝夕相处的伙伴。
猪,喂大了,卖了,明年再买一头小猪娃。
小女孩儿的指甲磨秃了,指关节早早变硬变粗了,柔柔的手再也回不来了。
我坐在田埂上,望着篮里满满的草,望着两个妹妹篮里满满的草,望着桃花篮里满满的草,望着雪芹篮里满满的草,望着田野里随处可见的草,我不知道草是我们还是我们是草。草一样的母亲,草一样的庄稼女人,我们这些似草一样谦卑的农家女孩儿,没有花样年华,就像这草一样枯萎了,埋葬在这泥土里,了无痕迹。
……
春风吹又生。
多年后,我站在一家商场的柜台前,很认真地为自己挑选一枚戒指。是的,为自己。结婚时,穷,婆家没有婚戒;现在,终于可以为自己精心挑选一枚戒指了。但千挑万选,竟没有一枚合适的款项。戒指花样繁多,品种琳琅满目,每款戒指戴在那柜台女孩儿的手指上,犹如蝴蝶落在绚丽的花瓣上,令人心生欢喜。柜台女孩儿的手肤如凝脂,柔若无骨,纤纤十指,鲜嫩得如破土而出的竹笋芽儿。再看看老妇的手,指头条粗得一如棍棒,戒指太精巧,根本就套不上手指。柜台女孩儿笑着说:“阿姨,说句你不爱听的话,你的指头太粗了,根本就套不上,这哪像一个女人的手……”刹那间,一切都复活了:麦地、野菜、竹篮、姐妹、小伙伴,我是田野里的草,是蓬蓬勃勃、皮皮实实、在大地里生长无拘无束的草,我不属于这牢笼般的商场,不属于这柜台里的精致华贵,我只属于活泼泼的土地,活泼泼的村庄。
活泼泼的村庄已不是旧时的模样。昔日和草整日打交道的农家女今也玩起了苹果电脑,她们在电脑上搜集千姿百态的秧歌,然后揉进她们劳动的元素,编成属于农民自己的独特风格。
清风、明月相伴。村里的广场闹起来,咱庄户人家的女人舞起来。
马大娘来了,李婶来了,麦穗姑来了,张嫂来了,芹姐来了,彩云妹来了;老的来了,少的来了,忙碌了一天的村里女人都来了。
江南雨的音乐响起来,北江美的音乐响起来,紫竹铃风的音乐响起来,凤凰传奇的音乐响起来……
一首首、一曲曲……村里的女人就这样开心地扭着、跳着、舞着,一如大地上碧绿的麦田,随风摆动,摆动出万千妩媚,摆动出日月精华,摆动出金浪滚滚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