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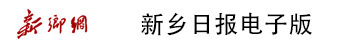


我读过的每一本书
王春花
多年以前,我偷看了二哥带回家的书,二哥问我见了没有,我打算看完给他放回去,所以硬着头皮说,没见。二哥不信,最后还是翻找出来,一脚把我从老当铺的台阶上跺下来。我骨碌下去时,台阶沿好像坚硬的书角硌着骨头。二哥站在台阶上怒目咬牙,说,叫你再敢偷我的书看!我爬起来揉揉疼的地方,下次见了还偷。大脑里好像住着一个贪吃鬼,只要纸上带字我就要用眼睛把它过滤掉。为此,我撞过电线杆,吃过灯油,直到今天忆起,嗓子眼儿仍会条件反射般不舒服。当习惯浸入骨血、肌肉形成本能,我读过的每一本书开始对我渗透、滋养、改造、塑形……
我做过一个梦。我在一千公尺的上空缓缓移动。脚下是纤陌纵横、森林、河流,一群鸽子贴近了我,我能听到它们扇动翅膀的声音。目光所及没有困囿,无边无际,灵魂轻盈自由。我努力搜寻日常生活中与之相近的体验。不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唯我独尊,又能与自然与自己和平相处。这不是梦,应该更像一个寓言。一个内心强大、饱满的人一定会有如此辽阔的视野,透过万千迷障看清万事万物的真相,看到无垠,看到自己在天地之间所处的那个点,明白自己的局限。
达到这一步是各种因素合力而为,最紧要的莫过读书。
我的人生阅历告诉我,在这个世界上人分两种,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。也有一部分不读书的人,就像我91岁的老母亲,她虽不识字,却把人和事当书读了,所以她会时不时爆出“骡子大,马大,人不能大”“能吃过天饭,不说过天话”之类的佳句。
读书是人和书的双向寻找。万籁俱寂,夜晚降临,群山深处、荒漠之中有光熠熠,那光就是一本本书,一个个智者在远处、在暗透的地方引你奔赴。奔赴的目的不是物欲,不是所谓的成功,而是从书中看到大,看到宇宙无垠,星汉灿烂。隔着湖海洲洋看到“山那面住着神仙”。越临近光,越发现自身的卑微和渺小,就像书法习久了,明白“字是不可以乱写的”。意会语言之妙,譬如鲸死了叫“鲸落”,猪拉的屎叫“猪零”(还是一味中药),花椒的果实叫“椒目”,有一种粉叫“骚粉”。
智者圣贤的大德、审美、善意,润物无声。你未必会成为他们,但在奔赴的路上洞悉了善恶美丑,遇见了最好的自己。见到了想见的,避开了不想见的。虽非圣贤但亦无顽鲁,免去夜行无光累及他人。
我从书里不是看到了更多的书,而是看到了晚归时家中窗子里闪烁的那点暖黄、翠雀花在深秋中的一抹雾蓝、“叫天子”在碧空中的嘹亮,还有蛙声和鸣下“地虻牛”的一支独吟。
眼下,我老了,生病了,书于我又成了一剂良药。当我知道自己会死,知道一切都将烟消云散,书又一次救助了我。它让我了解潜意识,了解人的自我修复能力,学会与疾病和谐共存。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,太阳再也不会照耀到我,但我活过,我体验过。书像羽翼带我去过不曾去过的远方。我也有大雪纷飞的日子,也有嚎啕的夜晚,但正是这些悲伤的底色,浑厚、立体、滚烫了我的人生。
人间值得。
(作者系原阳县退休干部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