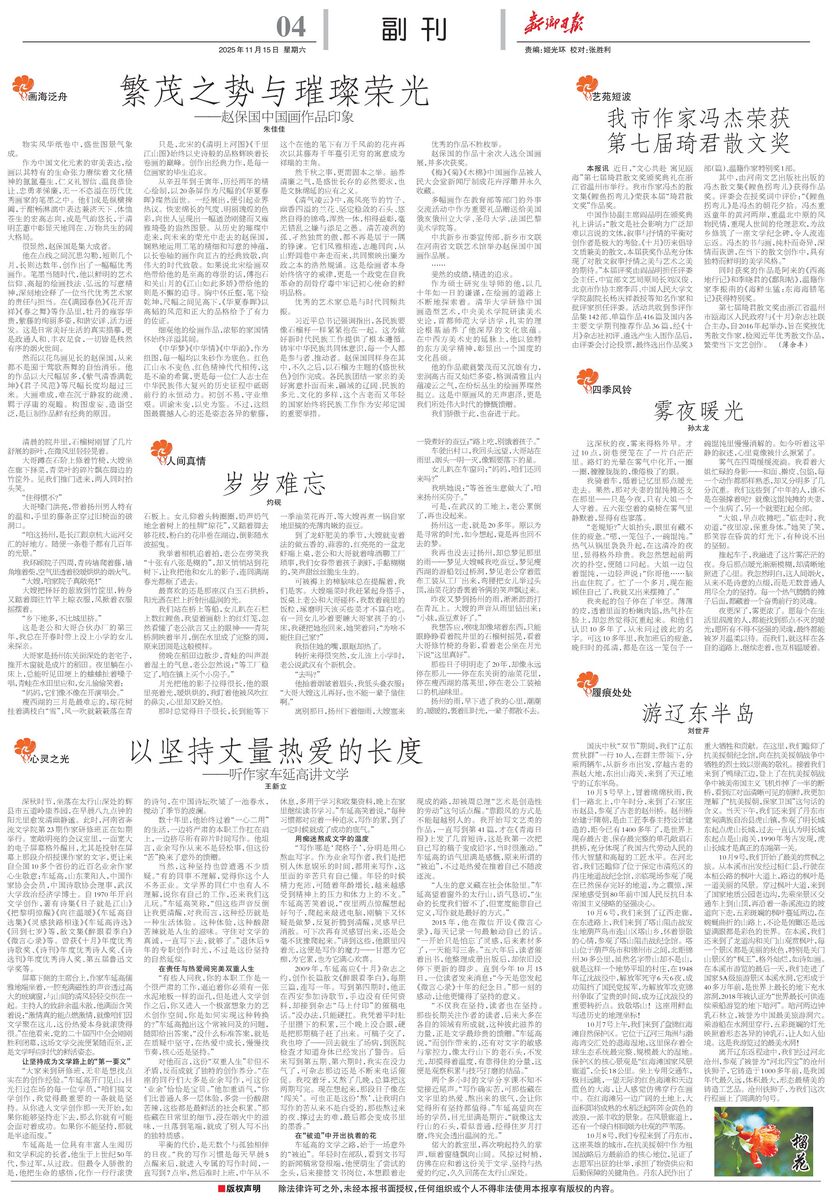以坚持丈量热爱的长度
发布时间: 信息来源:
——听作家车延高讲文学
王新立
深秋时节,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辉县市五道岭康养园,在早晨八九点钟的阳光里愈发清幽静谧。此时,河南省奔流文学院第23期作家研修班正在如期举行。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,一面宽大的电子屏幕格外醒目,尤其是投射在屏幕上那段介绍授课作家的文字,更让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的近百名业余作家心生敬意:车延高,山东莱阳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诗歌协会理事,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。自1970年开启文学创作,著有诗集《日子就是江山》《把黎明惊醒》《向往温暖》《车延高自选集》《灵感狭路相逢》《车延高诗选》《回到七岁》等,散文集《醉眼看李白》《微言心录》等。曾获《十月》年度优秀诗歌奖、《诗刊》年度优秀诗人奖、《诗选刊》年度优秀诗人奖、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。
屏幕下侧的主席台上,作家车延高儒雅地端坐着,一腔充满磁性的声音透过高大的玻璃窗,与山间的清风轻轻交织在一起。主持人的致辞余温未散,他满面含笑着说:“激情真的能点燃激情,就像咱们因文学聚在这儿,这份热爱本身就滚烫得很。”在他看来,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刚刚胜利闭幕,这场文学交流便紧随而至,正是文学呼应时代的鲜活姿态。
让坚持成为文学路上的“第一要义”“大家来到研修班,无非是想找点实在的创作经验。”车延高开门见山,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学员,“咱们搞文学创作,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。从你进入文学创作那一天开始,如果你能够坚持走下去,那么你就有可能会面对着成功。如果你不能坚持,那就是半途而废。”
车延高是一位具有丰富人生阅历和文学积淀的长者,他生于上世纪50年代,参过军,从过政。但最令人骄傲的是,他把生命的感悟,化作一行行滚烫的诗句,在中国诗坛吹皱了一池春水,搅动了季节的波澜。
数十年里,他始终过着“一心二用”的生活,一边将严肃的本职工作扛在肩上,一边挤尽所有碎片时间写作。他坦言,业余写作从来不是轻松事,但这份“苦”换来了意外的馈赠。
当然,这种坚持也曾遭遇不少质疑。“有的同事不理解,觉得你这个人不务正业。文学界的同仁中也有人不理解,说你有自己的工作,还来我们这儿玩。”车延高笑称,“但这些声音反倒让我更清醒,对我而言,这种经历就是一种生活体验。这种体验,这种酸甜苦辣就是人生的滋味。守住对文学的真诚,一直写下去,就够了。”退休后9年的专职创作时光,不过是这份坚持的自然延续。
在责任与热爱间完美双重人生
“有些人问我,你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很严肃的工作,逼迫着你必须有一张水泥地板一样的面孔,但是进入文学创作之后,你又进入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艺术创作空间,你是如何实现这种转换的?”车延高抛出这个常被问及的问题,随即给出答案,“没什么标准答案,就是在质疑中坚守,在热爱中成长,慢慢找节奏,核心还是坚持。”
对他而言,这份“双重人生”非但不矛盾,反而成就了独特的创作养分。“在座的同行们大多是业余写作,可这份‘业余’恰恰是宝贝。”他加重语气,“你们比普通人多一层体验,多尝一份酸甜苦辣,这些都是最鲜活的社会积累。”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细节,浸在烟火中的滋味,一旦落到笔端,就成了别人写不出的独特质感。
平衡的代价,是无数个与孤独相伴的日夜。“我的写作习惯是每天早晨5点醒来后,就进入专属的写作时间,一直写到7点半,然后准时上班,中午从不休息,多用于学习和收集资料,晚上在家里继续读书学习。”车延高笑着说,“每种习惯都对应着一种追求,写作的累,到了一定时候就成了成功的底气。”
用痴迷熬成文字的温度
“写作哪是‘爬格子’,分明是用心熬血写字。作为业余写作者,我们是把别人休息娱乐的时间,都用来写作,这里面的辛苦只有自己懂。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,可随着年龄增长,越来越感受到精神上的压力和体力上的不支。”车延高苦笑着说,“夜里两点惊醒想起好句子,爬起来敲进电脑,刚躺下又怀疑是做梦,反复折腾到清醒,灵感早已消散。可下次再有灵感冒出来,还是会毫不犹豫爬起来。”讲到这些,他眼里闪着光,这便是写作的魔力——甘愿为它痴,为它累,也为它满心欢喜。
2009年,车延高应《十月》杂志之约,创作长篇散文《醉眼看李白》,每期三篇,连写一年。写到第四期时,他正在西安参加诗歌节,手边没有任何资料,却接到杂志“马上付印”的催稿电话。“没办法,只能硬扛。我凭着平时肚子里攒下的积累,三个晚上没合眼,硬是把那期稿子赶了出来。可稿子交了,我也垮了——回去就生了场病,到医院检查才知道身体已经发出了警告。后来写到第五期、第六期时,我实在没力气了,可杂志那边还是不断来电话催促。我咬着牙,又熬了几晚,总算把这两期写完。现在想起来,那段日子像在‘闯关’。可也正是这份‘熬’,让我明白写作的苦从来不是白受的,那些熬过来的夜、撑过去的难,最后都会变成书里的墨香。”
在“被迫”中开出执着的花
车延高的文学之路,始于一场意外的“被迫”。年轻时在部队,看到文书写的新闻稿常登报端,他便萌生了尝试的念头,后来接替文书岗位,本想跟着走现成的路,却被周总理“艺术是创造性的劳动”这句话点醒。“靠跟风的方式是不能超越别人的。我开始写文艺类的作品,一直写到第41篇,才在《青海日报》上发了几首短诗,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写的稿子变成铅字,当时很激动。”车延高的语气里满是感慨,原来所谓的“被迫”,不过是热爱在推着自己不随波逐流。
“人生的意义藏在社会体验里。”车延高望着窗外的太行山,语气恳切,“生命的长度我们管不了,但宽度能靠自己定义,写作就是最好的方式。”
2015年,他在微信开设《微言心录》,每天记录一句最触动自己的话。“一开始只是怕忘了灵感,后来素材多了,一天能写三条。”五六年后,读者催着出书,他整理成册出版后,却依旧没停下更新的脚步。直到今年10月15日,一位读者发来消息:“今天是您发起《微言心录》十年的纪念日。”那一刻的感动,让他更懂得了坚持的意义。
“不仅我在坚持,读者也在坚持。那些长期关注作者的读者,后来大多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成就,这种彼此滋养的力量,正是文学最珍贵的馈赠。”车延高说,“而创作带来的,还有对文字的敏感与掌控力,像太行山下的老石头,不发光,却摸得着温度,有靠得住的分量,这便是观察积累与技巧打磨的结晶。”
两个多小时的文学分享课不知不觉接近尾声。“写作确实苦,可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热爱、熬出来的底气,会让你觉得所有坚持都值得。”车延高望向在场的学员,目光里满是期许,“就像这太行山的石头,看似普通,经得住岁月打磨,终究会透出温润的光。”
偌大的教室里,再次响起持久的掌声,顺着窗缝飘向山间。风掠过树梢,仿佛在应和着这份关于文学、坚持与热爱的约定,久久回荡在太行山深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