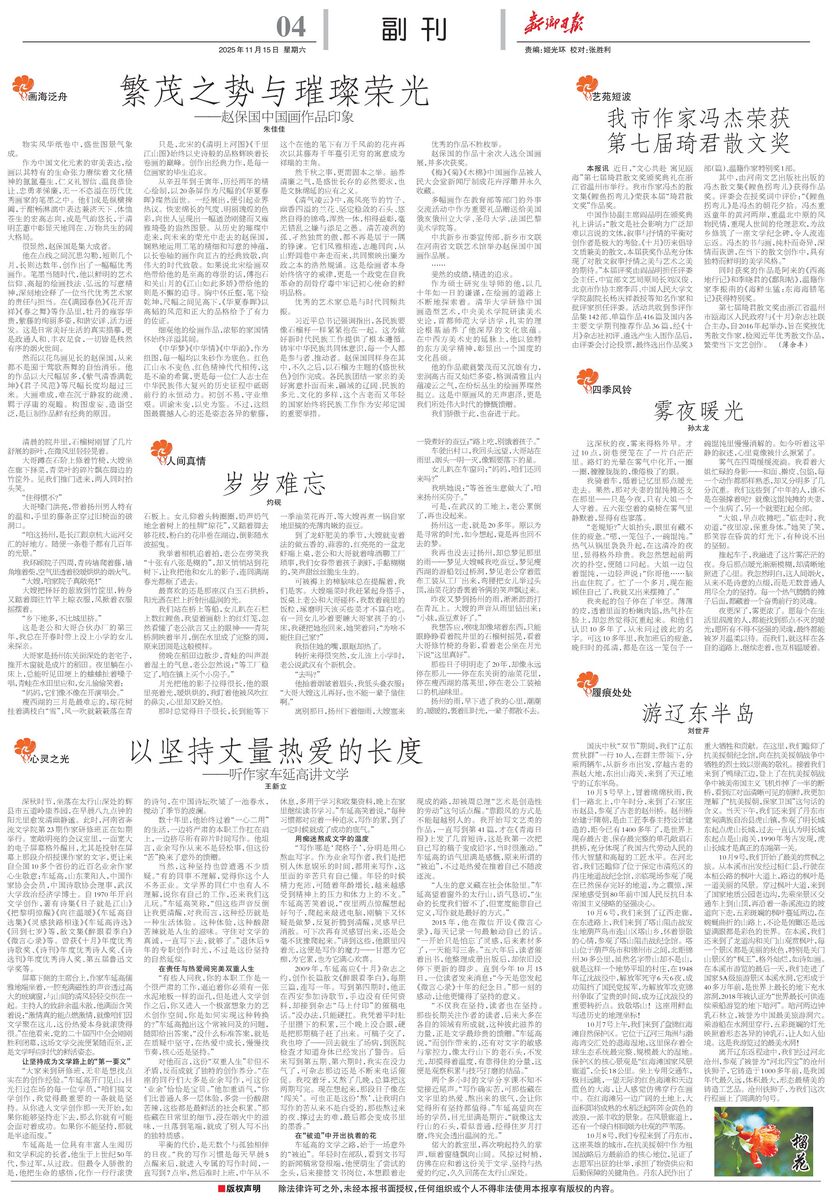岁岁难忘
发布时间: 信息来源:
灼砚
清晨的院井里,石榴树刚冒了几片舒展的新叶,在微风里轻轻晃着。
大哥蹲在石阶上修着竹椅,大嫂坐在廊下择菜,青菜叶的碎片飘在脚边的竹筐外。见我们推门进来,两人同时抬头笑。
“住得惯不?”
大哥嗓门洪亮,带着扬州男人特有的温和,手里的藤条正穿过旧椅面的破洞口。
“咱这扬州,是长江跟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好地方。随便一条巷子都有几百年的光景。”
我环顾院子四周,青砖墙爬着藤,墙角堆着柴,空气里透着股暖烘烘的烟火气。
“大嫂,咱家院子真敞亮!“
大嫂把择好的葱放到竹筐里,转身又踮着脚往竹竿上晾衣服,风掀着衣服摇摆着。
“乡下地多,不比城里挤。”
这是老公和大哥合伙办厂的第三年,我总在开春时带上没上小学的女儿来探亲。
大哥家是扬州东关街深处的老宅子,推开木窗就是成片的稻田。夜里躺在小床上,总能听见田埂上的蛐蛐扯着嗓子唱,青蛙在水田里应和,女儿偷偷笑着:
“妈妈,它们像不像在开演唱会。”
瘦西湖的三月是最难忘的,琼花树挂着满枝白“雪”,风一吹就簌簌落在青石板上。女儿仰着头转圈圈,奶声奶气地念着树上的挂牌“琼花”,又踮着脚去够花枝,粉白的花串垂在湖边,倒影随水波摇曳。
我举着相机追着拍,老公在旁笑我“十张有八张是糊的”,却又悄悄站到花树下,让我把他和女儿的影子,连同满湖春光都框了进去。
最喜欢的还是那座汉白玉石拱桥,阳光洒在栏上折射出温润的光。
我们站在桥上等船,女儿趴在石栏上数红鲤鱼,我望着画舫上的红灯笼,忽然看懂了老公欲言又止的眼神——青灰桥洞映着半月,倒在水里成了完整的圆,原来团圆是这般模样。
傍晚在稻田边散步,青蛙的叫声混着湿土的气息,老公忽然说:“等工厂稳定了,咱在镇上买个小房子。”
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他的眼里亮着光,暖烘烘的,我盯着他被风吹红的鼻尖,心里却又盼又怕。
那时总觉得日子很长,长到能等下一季油菜花再开,等大嫂再煮一锅自家地里摘的壳薄肉嫩的蚕豆。
到了龙虾肥美的季节,大嫂就变着法的做五香的、蒜蓉的,红亮亮的一盆龙虾端上桌,老公和大哥就着啤酒聊工厂琐事,我们女眷带着孩子剥虾,手黏糊糊的,笑声甜丝丝脆生生的。
可被褥上的樟脑味总在提醒着,我们是客。大嫂端菜时我赶紧起身搭手,饭桌上老公和大哥碰杯,我数着碗里的饭粒,琢磨明天该买些菜才不算白吃。有一回女儿吵着要睡大哥家孩子的小床,我硬把她抱回来,她哭着问:“为啥不能住自己家?”
我捂住她的嘴,眼眶却热了。
转折来得很突然,女儿该上小学时,老公说武汉有个新机会。
“去吗?”
他抽着烟皱着眉头,我低头叠衣服:“大哥大嫂这儿再好,也不能一辈子借住啊。”
离别那日,扬州下着细雨,大嫂塞来一袋煮好的蚕豆:“路上吃,别饿着孩子。”车驶出村口,我回头远望,大哥站在雨里,烟头一明一灭,像颗要落下的星。
女儿趴在车窗问:“妈妈,咱们还回来吗?”
我哄她说:“等爸爸生意做大了,咱来扬州买房子。”
可是,在武汉的工地上,老公累倒了,再也没起来。
扬州这一走,就是20多年。原以为是寻常的时光,如今想起,竟是再也回不去的梦。
我再也没去过扬州,却总梦见那里的雨——梦见大嫂喊我吃蚕豆,梦见瘦西湖的游船划过桥洞,梦见老公穿着蓝布工装从工厂出来,弯腰把女儿举过头顶,油菜花的香裹着爷俩的笑声飘过来。
昨夜又梦到扬州的雨,淅淅沥沥打在青瓦上。大嫂的声音从雨里钻出来:“小妹,蚕豆煮好了。”
我想答应,喉咙却像堵着东西,只能眼睁睁看着院井里的石榴树摇晃,看着大哥修竹椅的身影,看着老公坐在月光下说“这里真好”。
那些日子明明走了20年,却像永远停在那儿——停在东关街的油菜花里,停在瘦西湖的落英里,停在老公工装袖口的机油味里。
扬州的雨,早下进了我的心里,潮潮的,暖暖的,裹着旧时光,一辈子都散不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