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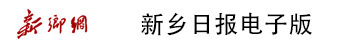


阳光里的麦香
一兵 (辉县市)
接爸妈来城里住三四天了,天一直阴着脸,昨天还下起了雨。爸嘟囔着:“麦子要熟了,天不能这个样子啊,该晴好了。”
“是啊,这天,影响麦子灌浆饱籽啊。”妈也附和着说。
“咱家没有地了,你们还管它天阴还是晴啊!”我对爸妈说。
“没有地是没有地了,可这小满季节是麦子灌浆饱籽的关键时期啊,这老天爷逆天啊。”爸看着我说。
家里原有的三亩多地,都靠父母打理的。去年秋天,家里的地被一个农贸市场立项征收了。耕种了大半辈子的土地,说收就收走了,二老心里总有点儿不情愿。
小时候的“六一”前后,放学回到家,街门经常锁着,我和弟弟就依偎在门口等。下晌后,妈拔开煤球炉的塞子开始做饭,爸坐在正间八仙桌旁的椅子上抽烟。“六一”假期,我和弟弟经常会被领着下地干活,老天爷热得弟弟发誓说一定得好好学习,将来绝不再下地干活受罪了。
地被征走了,爸妈闲得倒像没了魂一样,心里还操心着小麦成熟收割的事。
儿时小麦即将成熟时,爸会带着我们到田间地头,揪个麦穗查看,在布满老茧的大手里揉搓一下,嘴一吹,麦芒和麦壳被吹走,留下一把青色的麦粒在爸手心里。爸让我吃,我嚼了嚼,青涩难咽,吐了。爸把剩余的青麦粒一口放到自己嘴里,津津有味地嚼着,脸上荡漾着丰收的喜悦。
晌午下晌,妈会拿几根带秆的青麦穗回家,伸到煤球炉上的锅底下,火焰炙烤中麦芒烧没了,烤过的麦穗被妈在手里揉成滚烫滚烫的圆溜溜的青麦粒。妈放到嘴里嚼,说很好吃。我尝了尝,依旧青涩,不好吃。妈却吃得很香。
爸妈想家了,我把他们送回了村里。
农贸市场,每天车水马龙,人来人往非常热闹。爸妈经常到市场里买米买面、买菜买肉、买各种调料。爸说:“以前咱是到地里种,到地里收,现在咱是到咱那地里买粮食了。这世道,真是不敢想啊。”
在街门口,爸妈看到村里的老伙计忙着收运自家的小麦,很羡慕。老伙计却说:“你们现在都成‘市民户’了,多得劲儿啊!我们那一片地啥时候会被征收啊?”老伙计的车上掉到地上几根零星的麦穗,爸急忙捡起来,吹一吹上面的土欲呼喊老伙计时,发现他已经跑远了。
妈说:“还是该忙活的时候忙点儿好啊,这个季儿在家里呆着,浑身不得劲儿呢!”
晌午回到村里,家里的街门像小时候一样锁着,我像小时候等爸妈下晌一样依偎在街门口。十二点半了还不见爸妈的影子,左等右等,爸妈终于开着老年三轮车回来了,两人汗流满面,高高兴兴地带回两大包麦穗。原来,爸妈去别人收割完的地里捡麦穗了。
妈忙着去做饭,爸把两包麦穗倒在太阳下晾晒。他一边摊开一边对我说:“瞧,差不多能磨出半袋面粉呢。”
“天这么热,你们可别因为捡拾个麦穗累出病来啊,咱又不缺这袋面。”我埋怨爸妈。
妈满脸喜悦地从厨房走出来说:“没事,活动活动心里才高兴,这个季儿窝在家里才难受呢。你看这麦穗,多好!”
看着爸妈摊到阳光下的麦穗,我也闻到了丝丝麦香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