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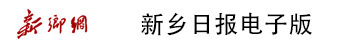


新一街的槐
|
芭蕉雨声 文/图 (新乡市)
新一街这条小路相对僻静,人来车往轻手轻脚。行道树乌嘟嘟的,清一水儿的槐。黑槐、笨槐都是小名儿,大名国槐。出芽迟,开花晚,真够笨的。好在我有耐心,相信它会有今天的浓荫。
雨后晨光斜透过来,地上阶梯式的暗影像是篦子梳过,我不忍下脚。保洁师傅一下一下去扫,扫不开。叶子想摇就摇摇,我望望这个,望望那个,都是我熟悉的模样,长在城里依然保持烟火本色,拙朴,憨厚,宽容。从疼痛的寒冬里冲将出来的每一片叶子都散发着苦味。我在路沿坐下来,任清澈的光影淋我一身。
动不动跑到这里来,来之前并没有想着它能带给我啥样好处,只是很单纯的想。
槐叶温柔繁荣,望来望去眼睛都是凉的。草木面前我是一个贪心的人,对自然美色比如叶啊花啊没有抵抗力也就罢了,印在地上的影子也在乎得不行。光影摇曳,不由人不去发呆遥想。
上次回老家与母亲坐在槐荫地儿闲聊,母亲仰头看看稠密的枝叶说,小满了,新叶能捋着吃了。还强调说只有到了小满才能吃,早了嫩叶有毒,过了小满十来天也行,再迟就不中了,苦。
小满吃槐叶我有印象。经母亲一说,味觉记忆在唇齿间复活,迎合着母亲的句句提醒,甜丝丝的,尤其吃一口蒸槐叶,喝一口绿豆汤,有回甘。对,正是这个回甘让我一直忘不掉又无力清晰复原,母亲在启发和激发那个隐秘的临界点。成功了,完全忆起来了。槐叶直接丢面条锅,焯水凉拌,拌面蒸,熬菜糊涂,很多吃法。到底俺俩也只是嘴上说说,没有动手去够那叶子。
母亲总是望着大树幽幽慢慢把话题扯得很长,念叨老院那棵老槐树的好,结槐米,够槐米,卖成钱给我缴学费。树高,站在东屋房顶、西屋房顶也不能完全够净,父亲就上到堂屋房一米多高的裙沿上,裙沿石板腾空,很危险。还上过望蓬顶,就更高了。后来父母年纪大了也听劝,不够了。再后来父亲不在了,母亲偶尔背着我们偷偷扒几枝,这两年是彻底不思念这事了。从开始的一季卖二三十块钱、一百块钱,我读初中、高中,随行就市越来越贵,卖五六百块钱也是有的。
母亲刻记老槐树的功劳,夸它是俺家功臣。年年都要在槐荫里复述几遍,意在感恩。
城里的树,不止黑槐,每一棵都让我心生敬意,它们不比空气洁净的山里,叶子是带着责任出场的。过滤汽车尾气、吸附工业污染物、给行人遮凉阴,我珍视树木赐予人世的这分恩情。又无法言说,只能一次次跑来与树们待一会儿,拍个照,摄个影,润润心。
很平常的槐荫凉街短视频发出,不少人发出沉浸式感叹,夸它是人间天堂,说小时候几乎每条道路都是这样,树荫亭亭如盖,孩子们放学溜达着慢慢回家。现在车多拥挤,老城区很难见到这原始森林般的街景。我便很欣慰,守得这片清净地。
槐米还没有露头,隐约鼓起一星星儿蕾苞。夏日的好全在这里,幽寂、宁静、松弛,树下流连总也不想回去。下次带点儿干粮,就可以待久一点儿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