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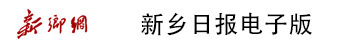



从“读”到“写” 受益终生
刘长利
要问读书的益处,我的体会是:如能博览群书并学以致用,就能化平凡为神奇,甚至改变命运。
我的阅读是从小人书起步的。那年,父亲从省干部疗养院调至新乡专署干部疗养院(均位于现卫辉市)。搬家仓促,我家暂居于院里的图书馆。五六岁的我,感觉一排排书架高不可攀,倒是最下层的小人书伸手可得。大半年时间,只认识“人”“口”“天”“大”的我,兴致勃勃地“博览”了几百本画册。
等我上四五年级产生强烈的读书欲望时,却没有了驻扎在图书馆的便利。正值“文革”时期,能见到的只有寥寥几本红色经典,读小说、名著成了奢侈。一次捡到一本缺皮少页繁体竖排的《水浒传》,居然让我连猜带蒙读得欲罢不能。由此勾出馋虫,饿狼般到处踅摸“禁书”。恰好当时的汲县师范被解散,大量馆藏图书被送往造纸厂,有些书幸运地被爱书人士截留,悄悄在社会上流传。我趁机到处“撒网捞鱼”,逮着什么读什么,大多是险遭厄运的长篇小说。记得有“三朵花”和“家春秋”系列、前苏联的经典小说,中国的四大名著以及世界名著等。读得走火入魔时,曾因深夜打手电看《三言两拍》被父亲揪出被窝;课堂上老师讲得口若悬河,我把《红与黑》放在课桌斗里看得如痴如醉。有次体育课被同学强拽到篮球场,可我还在想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滑稽相,结果被一个传球砸了个满脸花。
中学阶段,我的主要精力几乎都用在了找书、看书上,不论古今中外,只要是小说就爱不释手,一旦找到好书,便夜以继日,魔怔一般。曾将《红楼梦》中的生僻字,逐一查核记下,有些经典片段还能背下来。
读书多了,我的语文水平迅速提升,写作文时,摘录的大量好词好句派上了用场,作文经常在班上宣读,还不时在校广播站“发表”。
读书多了,就想“比葫芦画瓢”地写。上世纪80年代初,作家张斌在豫北医专(新乡医学院前身)工作。我怀揣几篇习作登门求教,他毫不客气地告诉我,写的不是小说,是故事。虽然小说靠故事情节推动,但怎样塑造人物形象,写出独特的“这一个”才是关键。这会儿方明白,我的“写作”和真正的文学是不搭界的。他让我读他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的那些小说,还推荐了不少名家名著,嘱咐我要精读,要揣摩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书是要这样去读的。我开始转变阅读方式,完成了从“量”到“质”的跨越,并师从张斌开始小说创作。1982年,《百花园》发表了我7000字的小说处女作。后来我读河大汉语言专业,系统的理论学习,古今中外的大量阅读,加上之前的积淀,为圆作家梦打下了基础。之后,我把自己牢牢绑在文学创作的马车上,一路颠簸走来。
前年,申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整理上报创作成果时,我自己都吃了一惊,这些年发表出版的文学作品居然有200多万字,还获得了不少大奖。由读者变作者,让我深有体会:读书虽说是“开卷有益”,但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,读书要讲究技巧,要“活学活用”,力戒“死读书”“读死书”,只有把书的营养转化为自己的养分,才能“学以致用”,给自己带来受用不尽的益处。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