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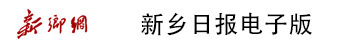


不熄的煤油灯
刘传俊 (郑州市)
那时,家乡不通电,每到晚上,屋子里一片漆黑,院子里一片漆黑,整个村庄也是一片漆黑。若遇到月明星稀的夜晚,我幼小的心田里便明亮起来,像要过年节一样兴奋异常,约上三五个小伙伴儿在村庄里疯个够。
我所居住的村庄离城市并不遥远,只有区区九公里。但因它不属于市郊而属于县里的地盘,夜晚常被漆黑笼罩着。见了“动静”的土狗那几声狂吠,更觉声音幽远。
当时我还小,不知为何大人们都叫“煤油”为“洋油”。直到上级发话,大意是说这油是我国自行生产的,这叫自力更生,这叫大涨国人的志气,乡人才统称“洋油”为“煤油”。从此,称呼“洋油”的历史一去不复返。
煤油灯有用墨水瓶做的,也有用比墨水瓶稍高、粗一点的药瓶子做的。从瓶盖处钻个圆孔,用薄铁皮卷个细圆筒插在里边,再用棉线或棉纸之类搓成捻子,让这捻子穿过薄铁皮细筒浸到瓶内的煤油里,一盏煤油灯便做好了。我家的两盏煤油灯就是这样做成的。一盏放在北屋灶火用三合土打的西山墙中部挖的洞里,另一盏放在东屋正间那张黑色方桌上。
天完全黑下来了,母亲做饭时点亮了如豆的煤油灯。昏黄的灯光,映照着烟熏火燎了好多年的灶火,和墙壁上似要脱落下来的黢黑的痂。母亲好像是时间的奴隶,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揽过来由自己支配。冬天晚饭刚过,她顾不上取下右手中指戴着的那个铝制顶针就洗刷起来。顶针和碗筷、勺子相遇的摩擦声,听起来十分富有质感。顶针的光在煤油灯的映射下一闪一闪的,很有节律。末了,母亲将剩饭、红薯皮混合抓碎,温热后去喂嗷嗷待食的猪娃。这些事做完,堂屋里那盏煤油灯又亮了。母亲将煤油灯端下来,放置于盘腿而坐的纺车怀里,在煤油灯光的弥漫中一纺就是大半夜,甚至鸡叫三遍。夜深人静,饿、冷、困相继袭来,她有时就在纺车怀里打个盹儿,睁开眼又继续纺线。纺线似乎是母亲的专利,白天在地里劳累了一整天的她,一年到头,几乎每晚都是如此。母亲常说头晕,那是常年劳苦熬夜、营养不足所致。全家人床上铺的盖的,身上从内到外穿的,哪一件不是母亲在煤油灯下纺出来、做出来的?母亲究竟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,只有那盏煤油灯知道。煤油灯以微弱的光亮照耀着我们那个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家庭,也照耀着母亲的儿女们成长的道路……
有人家必有煤油灯,就连生产队里的牛屋、磨坊里也备的有。但煤油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储备的。点灯时分,有的人家就端着空油灯走东家跑西家去“讨借”。可能是因白天忙没顾上打油,也可能是因从年头到年尾面朝黄土背朝天,没有进项,手头拮据,缺少钱去打两毛钱一斤的煤油,能撑一晚是一晚。实际上,晚上不点灯的也大有人在。村里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,其父给他两毛钱让他去供销社打煤油。他用一毛钱打了煤油,一毛钱买了零食。油量明显不够,过河时,他往透明的玻璃瓶内掺了水。晚上点不着灯,其父果然察出了端倪,他招来的自然是一顿打骂。后来,其父让他顶烈日在野地里挖了三天“半夏”到城里卖钱,这才弥补了他不知苦寒生活滋味的“过失”。
“鸡蛋换盐,两不见钱”是我们那一带的口头禅。村里有的人家理应中午放盐的面条饭,却因没钱购买只好喝淡的。我家从未“讨借”过别人家的煤油、食盐等生活用品,是因有一位勤劳的母亲在支撑那个摇摇欲坠的家。初春,母亲总要千方百计买回来一些鸡娃儿喂养。若天气咋暖还寒,她就用棉衣将盛放鸡娃儿的竹笼子遮盖上,生怕小生命夜间受冷、受伤害。晚上,只有将它们搁在床边,母亲心里才觉踏实安稳。新鸡、老鸡接上了茬,下了蛋拿到供销社兑换煤油等生活必需品,似乎成了我家唯一的进钱门路……
清苦日子用手指掐着、过着、熬着、盼着,年年岁岁,周而复始。每隔一段时间,母亲就会让我兜几个鸡蛋,去隔一条小河叫“窑场”的村庄里的供销社换煤油。一日晚归,一不小心,小河中那块过脚石被我踩滑,母亲给我做的布鞋全湿透了。我把鞋悄悄放在做饭后的锅底里,想让余热焙干。没想到,灶火里的余热威力不减,翌日早晨再穿时,发现布鞋竟被烤糊了。看到母亲在煤油灯下千针万线给我做的新布鞋几乎化为灰烬,我心疼得直掉泪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我,晚上写作业、读书时,总嫌煤油灯头太小不明亮,过一会儿就用做衣服的大针往上挑拨捻子。正在纺棉线的母亲见状,总让我往下按一按灯头,生怕灯头大了浪费煤油。那煤油,是母亲煞费苦心每天无数遍“咕咕咕”叫着养鸡,用鸡蛋换回来的。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大年三十傍晚,我家通电了!母亲将包水饺的面皮从灶火端到堂屋一侧的厢房内,在昏黄的灯光下喜气洋洋包着团圆饺子,少见的笑容写在了她的脸上。从此,祖祖辈辈没有用过电的那页历史被翻了过去。村村户户都通了电,我看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。
后来,我来到城市打拼,当看到夜幕降临,林立的高楼、宽阔的街道灯火辉煌时,我若有所思:当年的煤油灯功不可没,是它照亮了我脚下的路,逐步引导我走进了这个鲜丽光彩的城市里。
时间宛如窗间过马,过往的人和事不计其数,不知道小小的煤油灯照亮过多少步履匆匆的路人。但我心里清楚,我便是那万千者之一。我微微仰起头,闭上眼睛,眼前似乎有如豆的煤油灯穿越时空般一扑闪一扑闪在晃动,心房里似乎也有如豆的煤油灯的马蹄踏过……

